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3月发生的“邯郸初中生遇害案”再次引发了大众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和刑事责任年龄的关注和讨论,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也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该条款将刑事责任年龄有条件地个别下调到12周岁,使前述案件中年龄为13周岁的犯罪嫌疑人有了被刑罚制裁的可能。2024年4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通报称,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这对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示范意义”。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和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十二年,对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中国法制史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存在“杀人偿命”的理念,但对于未成年人或者说少年儿童的杀人行为,统治者在立法上往往给予一定宽宥以彰显仁慈。这种宽宥在制度化、明文化后,与现代的刑事责任年龄有着共通之处。不过,古代矜幼原则却并非不可突破,历史上存在大量突破这一原则的案例。通过观察古代审理者在审判身为重犯的少年儿童时,会因何种原因对其适用通行规则,又会在何种情况下作出突破通行规则的判罚,提取其中具有现实意义的考量因素,可以为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能力判定规则及其应用,尤其是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中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提供有益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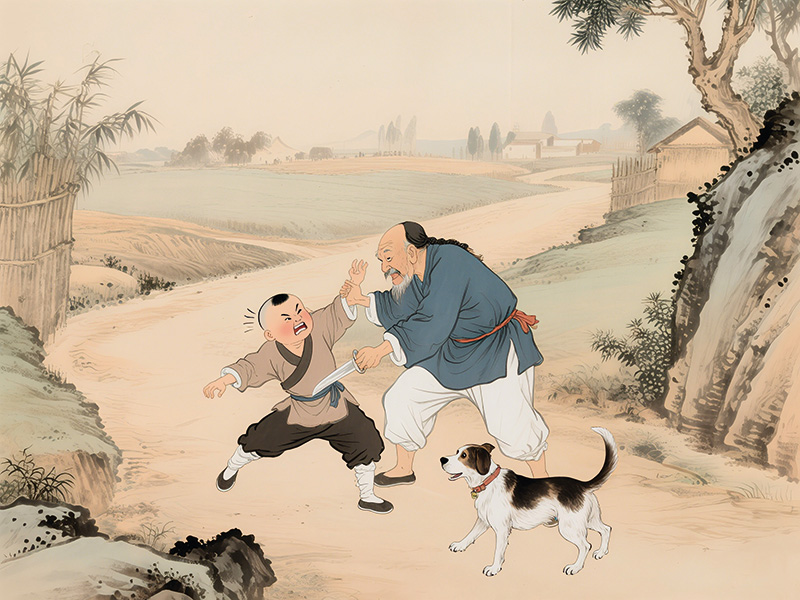
乡间小道,年长力强的丁狗仔欺凌丁乞三仔,丁乞三仔愤怒无奈并做出杀伤举动(AI技术生成)
二、中国古代少年刑事司法的特殊判例
《魏书·刑罚志》记录了南北朝时期北魏延陵地区发生过的“月光童子刘景晖案”。熙平年间,王买谋反叛乱,时年9岁、号称“月光童子”的刘景晖参与了叛乱活动。由于“月光童子”一词在魏晋南北朝长期被用于政治宣传,成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宗教象征,依佛教典故解读,“月光童子的出现代表着将有新君出世”,因此在平定叛乱、抓获叛首后,如何处置刘景晖成为一个与如何处置主谋王买近乎同等重要的决断。对于王买的处罚因为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过多讨论,而关于如何处置9岁的刘景晖,统治阶级出现了意见分歧。廷尉卿裴延俊提出“合死坐正”的意见。而大理正崔纂则认为所谓“月光童子”是地方官员意图冒功而强加于刘景晖的,虽然刘景晖也有一些“能变为蛇雉”的言论,但是其“口尚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己”,所言不过附和他人而已,因此建议免其死刑。灵太后最终听取了崔纂的建议。
《旧唐书·刑法志》载有一件“救父殴杀案”,最终也获得了免去死刑的结果。该案中,死者张莅欠康宪钱粮未还,康宪携子上门讨债,张莅醉酒之际制服康宪并险些令其窒息。康宪的儿子康买得想要救下父亲,因此用木锸打击张莅的头部致其3天后死亡。由于康买得当时已经14岁,按照唐律已经达到对杀人行为负责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处死刑。但当时的刑部员外郎孙革认为,康买得的行为动因是救父而非行凶,因此上请减轻处罚,最终获准。然而,并非所有以亲情为由的杀人行为都能得到统治者的宽宥。《旧唐书·孝友传》记载的“张瑝兄弟复仇案”中,张瑝、张琇两兄弟认为其父被万顷等人构陷杀害,于是伺机杀死了万顷并准备继续杀死其他参与构陷之人,但在流亡途中被捕。虽然当地百姓认为张瑝兄弟二人尚系少年却能为父报仇而对二人抱有极大的同情,甚至中书令张九龄也为之请命,但是唐玄宗不为所动,最终张瑝两兄弟被处死。两案之间的差别引人深思。
《宋会要辑稿》中有4例关于少年儿童犯罪的案件,但篇幅都比较短,也没有记载审判时的讨论和考量。一是“蜀州从行劫贼案”。宋太宗至道二年,蜀州一个10人的劫掠团伙被抓捕,其中有一人年仅13岁,系在其父命令下携带兵器跟随团伙行动。宋太宗念其年幼无知,在刑罚上予以宽待。二是“宁州殴杀案”。宋仁宗天圣元年,宁州庞张儿殴杀庞惜喜,审刑院经审理认为应当判处死刑。宋仁宗认为庞张儿只有9岁,在殴打中没有杀人的故意,是儿童之间的争斗,因此免除庞张儿死刑,判罚其对庞惜喜家进行赔偿。三是“益州坐怒殴杀案”。宋仁宗天圣十年,益州费进犯有前科,以财产赎刑,并受罚以奴婢身份听赵氏使唤。费进在被赵氏催讨欠款时怒不可遏,将赵氏殴打致死,依法应当处以死刑。由于费进年仅14岁,地方官员奏请皇帝发落,宋仁宗下调了量刑。四是“濠州争斫致死案”。宋仁宗景祐元年,濠州王泮奇同样犯有前科,在楚李婆家中服劳役。王泮奇因与楚李婆在劈木柴一事上起了冲突,用镰刀砍伤楚李婆致其死亡,依法应当处死。由于王泮奇年仅9岁,地方官员奏请皇帝发落,宋仁宗同样下调了量刑。
《明实录》中也有一些皇帝亲断宽宥减免少年儿童罪行的记录。例如《明实录·太祖实录》中记载的与前述唐代“救父殴杀案”类似的“顾父伤人致死案”。死者生前与人争执并用砖石投掷致人倒地,伤者年幼的儿子手持农耕器具在旁边,便打伤死者并致其死亡。刑部官员认为应当处以绞刑,但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处罚畸重,称“父亲被人伤害的时候,孩子只顾得上保护父亲,哪里顾得上遵守法律”,便免却其死刑。此外,《明实录·太宗实录》所载“未成人强盗案”中一段关于少年儿童犯罪的讨论也值得关注。该案中,一众强盗中有两人年龄在15岁以下,被皇帝免除死刑,但刑部官员认为二人既然已经能够实施抢劫行为,不应法外开恩免除死刑。明太宗(明成祖)朱棣答复:“儿童等未成年人本身认识不到行为的性质,若没有成年人引诱,又怎会成为强盗。况且二人连提起两斗粟米的力量都没有,若他们有秦舞阳、区寄的能力,我又怎会为他们破格免死?”
清代《刑案汇览》中也记载了大量关于少年儿童犯罪案件,而且相比于《宋会要辑稿》的简略,《刑案汇览》基本记载了案件审理和讨论的经过,对于探求当时审理者对于判罚结果的考量因素提供了依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丁乞三仔案”与“刘縻子与李子相案”,且前者成为指导性判例“历久遵行”。两个代表性案例的结果大不相同:前一个案件中,丁乞三仔的杀伤行为是由年长力强的死者丁狗仔的欺凌行为所引起,因此丁乞三仔被认为“情有可原”,故被从宽处理、免除死刑;后一案件中,杀人者刘縻子被认为“赋性凶悍”,不应立即减免其刑罚,应当收监看押、消磨戾气,以观后效。值得一提的是,《刑案汇览》中专门就未能参照“丁乞三仔案”减刑的案件进行了记录,包括“戴七砍伤彭柏子身死案”、“陈枚太致伤钟壬新身死案”、“杨文仲殴伤张兆熊身死案”、“熊照戳伤林奉身死一案”和“唐细牙因被王时颖扭住挣脱致王时颖跌伤身死”。
三、裁判思路的现代表达
纵观中国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与其说刑事责任年龄是一种规范意义上规则的确立与适用,不如说是观念意义上正义的衡量与校准。审判者并不将刑事责任年龄视作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在具体案件中,结合实际情况来决定犯下罪行的少年儿童是否可以得到宽宥。站在这一角度回望古代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则,我们发现其与现代刑事责任年龄规则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古代划定了一个相对较低的刑事责任年龄亦即面向少年儿童较大的刑罚适用范围,通过上请奏闻等方式,逐案将罪过不深的少年儿童免于刑罚尤其是死刑;现代划定了一个相对较高的刑事责任年龄亦即面向未成年人较小的刑罚适用范围,通过明文规定适用于特殊罪行、特殊情形的例外规则,依法对应负相应刑事责任的未成年犯给予刑罚处罚。简单来说,古代针对少年儿童犯重罪,以入罪为原则、出罪为例外;现代处置未成年人犯罪,以出罪为原则、入罪为例外。中国传统法律实践中的刑事责任年龄通行规则的适用,尤其是突破通行规则的特殊判例,其背后的考量因素可以为当今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规则的理解与适用提供借鉴,而这种借鉴因为具有文化心理上的历史传承而颇具现实价值。
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设置了五个适用要件,其中四个为实质要件,分别为年龄要件(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罪行要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如果是在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过程中又故意杀人、伤害的,也可依法适用)、结果要件(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要件(主客观方面综合评价要求情节恶劣),一个为程序要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程序要件的存在是为了明确对实质要件的判断权由谁行使,因此,只有准确理解四个实质要件的判断标准才能合理适用此条款。在四个实质要件中,年龄要件、罪行要件、结果要件要么本身就具有客观属性,要么在长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完善可靠、规范统一的客观标准,除“特别残忍手段”外并不具有太高的甄别难度。而且即便是“特别残忍手段”这一要素的判断,也只有判断尺度上可能存在的偏差,而无判断内容上的歧义。相较之下,情节要件“几乎可以容纳任何与犯罪行为相关的主客观事实”,不仅没有法定的判断尺度,甚至没有法定的判断内容。形象地说,其他三个要件是进入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视域的界碑,而情节要件是启动该条款的密钥。
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以来,已有不少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中情节恶劣认定范围的讨论。主流观点认为,对情节恶劣应当从主观恶性、社会影响以及犯罪结果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也有学者提出了“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的评价模式。从古代司法实践中汲取经验,也能对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中是否构成情节恶劣的认定提供判断思路。因此,在观察历朝历代普遍设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基础上,以何种情形作为个案调整的考量因素,对司法者理解和适用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规则中的情节恶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前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此条款讨论已不鲜见,但立足这一视角的讨论还未见诸学界。
(一)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
现代刑法学理论将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者在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上都存在区别。而古代刑事立法中虽无此区分,但在判例中已存在将对犯罪行为结果的主观态度作为突破刑事责任年龄的判罚依据。
唐朝的“救父殴杀案”和明朝的“顾父伤人致死案”较为类似,作出致死伤害的行为人主观上显然能够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但对于结果的发生,至少在当时的审理者看来,并不具备积极追求的主观态度。也就是说,二者都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制止死者对其父施加的伤害行为,而对杀伤结果抱有一种放任的态度。这也是现代刑法理论中所说的间接故意。古代审理者虽然并没有这类概念指导其作出判断,但朴素的认识使其明白二人“为父可哀”、“但知顾父”,这成为两人被特别宽宥的主要原因。虽古代注重孝道,社会普遍同情甚至赞许这类行为,但是这种观念绝非相应判例中免除死刑的关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唐朝的“张瑝兄弟复仇案”。在该案中,张瑝、张琇两兄弟抱着为父报仇的目的,筹划并实施了仇杀行为,具有明显的直接故意。二人被捕后,民间“多言其合矜恕者”,甚至朝中大臣也有人“欲活之”,但最终的审理者认为“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没有因为他们“幼稚孝烈”予以宽恕,下令“付河南府告示决杀”。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月光童子刘景晖案”中,无论刘景晖是否曾以“月光童子”自称,其参与叛乱谋逆活动的行为确凿无误,因此掌管司法的官员提出了“合死坐正”的量刑建议。然而,即便刘景晖犯下了这种在当时背景下居“十恶”之首的严重罪行,死刑建议最终竟没有被统治者采纳,而是突破当时的刑事责任年龄在罪名方面的适用限制,特别赦免了刘景晖的死刑。这一结果的背后,主要原因在于刘景晖“愚小”,没有积极追求的主观恶意,散布“妖言”也不过是“傍人之言”,本身没有树立宗教形象、动摇甚至推翻统治的意志。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清朝的“刘縻子与李子相案”。在这一判例中,与刘景晖同为9岁的刘縻子,所犯的殴杀罪行远远轻于刘景晖的谋逆罪行,然而最终却没能像刘景晖那样得到突破刑事责任年龄的宽大处理,而是在被地方官员作出“拟绞监候”的量刑建议后,又在上请环节中被皇帝认为“不宜遽为矜宥”,故采纳了地方官员的量刑建议。其关键原因在于刘縻子“殴毙人命”所展现的对自己行为性质的清晰认识和对行为后果的积极追求,也因此被认为“赋性凶悍”、“不宜遽为矜宥”。
上述“张瑝兄弟复仇案”与“救父殴杀案”同样发生在唐朝,却有着不同的结果;“月光童子刘景晖案”所犯罪行明显重于“刘縻子与李子相案”,但却能得到宽大处理,这均更能印证是否具有直接故意的主观态度确为古代审理者裁决相关案件时的考量因素。这背后的逻辑较为通畅:直接故意的犯罪行为尤其是杀人行为是对国家律法的直接挑战,转圜的余地极小,为了保证国家律法的权威与尊严,也不宜对相关少年儿童从宽处理。
(二)事前蓄意与临时起意
是否事先进行了对犯罪行为的谋划也是古代少年儿童犯罪案件审理时的考量因素之一,这一点在上述“张瑝兄弟复仇案”中也有所体现。在现代犯罪心理学理论中,将犯罪动机划分为预谋性犯罪动机和情境性犯罪动机。其中预谋性犯罪动机是在较长时间内通过多次思考形成的,而后者是在情境因素的作用下较短时间内迅速形成的,因为犯罪者事先没有思考和准备,所以这类犯罪动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具体的行为情境和犯罪人当时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情绪状态)决定的。通常来说,也被称为“蓄意”与“临时起意”。
宋朝的“益州坐怒殴杀案”、“濠州争斫致死案”均系少年儿童因为一时争执导致的突发性犯罪,属于上述所说“情境性犯罪动机”即临时起意的范畴,即便依照律法“合处死”,最终也能够得到突破刑事责任年龄的死刑减免优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考量因素虽在前面提到的唐朝“救父殴杀案”和明朝“顾父伤人致死案”等判例中都能够得到印证,但在清朝“陈枚太致伤钟壬新身死案”等判例中却未曾体现,这些其他犯罪情节较宋朝两个案例更轻的少年儿童激情犯罪行为都没有得到法外开恩。事实上,自“丁乞三仔案”以来,一般的激情犯罪已经不再被清朝的统治者认为属于“可矜”之情形,必须探究犯罪行为是否由他人在先的欺凌行为而激起。只有当少年儿童的杀伤罪行是为了制止或反抗欺凌时作出的,才可能被认为“情有可原”,进而“着从宽免死”。而且,这一条件下的欺凌行为之认定存在系列标准,包括欺凌者的年龄要高于被欺凌者4岁以上、欺凌行为长期存在或具有一定严重性等。这一高度细分的考量因素对于应对基于校园欺凌行为产生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具有启发作用。
(三)自发犯意与诱发犯意
宋朝的“蜀州从行劫贼案”和明朝的“未成人强盗案”还透露出一个关于少年儿童犯罪是否能够赦免死刑的考量因素,即犯罪故意是否由他人有意促成。对此,我们可将其区分为自发犯意与诱发犯意。由于少年儿童心智上天然存在的不成熟,他们的主观意志往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扰,也容易在他人的教唆、诱导、胁迫甚至是命令下作出犯罪行为。如果这类犯罪行为是短暂、少次、偶发的行为,则或许能够运用现代的间接正犯或者教唆犯的理论去解决相应问题,但若这类犯罪行为是长期、多次、频发的行为,由于最初被诱导的犯罪故意很可能在长期的犯罪行为中内化为本身的意志,这时如何对待这些在犯罪活动中后期已然能够辨认犯罪行为性质甚至积极追求犯罪行为后果的未成年人,便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段首提到的两个判例中能够发现,古代的审理者对于犯罪故意系在他人授意下形成的少年儿童,即便依法“该死罪”,也往往不判处死刑,甚至在司法官员提出“彼虽年幼,既能行劫,亦当被刑,不宜免死”的建议后,最终的审理者仍然坚持免死的判罚。不过,在有限记录中,我们能够发现,这种情形下犯罪的少年儿童,都是跟随团伙作案,没有犯下团伙犯罪行为以外的罪行。因此,或许在这一考量因素中,还暗含了“犯罪行为没有超过授意范围”这样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当少年儿童又积极主动地犯下了授意以外的其他罪行,或者在授意的罪行中造成了超过授意的后果,或许便不能享受刑罚优待。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历代王朝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回顾,我们发现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更具体地说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和适用体系虽在我国发轫已久,但历代统治者又往往突破刑事责任年龄的界限,对犯有死刑罪行、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但年龄偏小的行为人或“矜”或“宥”,形成了一种“个别上调”的审判惯例。这种情况犹如现代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一种镜像。古今法治水平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古代关于少年儿童犯罪处罚规则的立与破,对我们当代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则及其适用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通过前述梳理分析有关判例背后的审理思路和逻辑,可以发现古代审理者聚焦于行为人的主观条件。如果用现代刑法语言表达,这些主观条件具体包括行为人对杀伤行为是否出于直接故意、是否能够辨认行为的性质、在行为发生前是否已有蓄谋、犯罪动机是否为反抗严重欺凌行为、犯罪故意是否由第三人有意促成等。虽然在古代人治社会中,这些判例难免带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但是它们散布在超过一千年的中国法制史中,由不同的帝王、司法官员和地方官员参与,却还能呈现出较为突出的特点,这说明相关判例已经能够实现统治者抚慰民众的效果,进而证明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共识。这种共识延绵至今又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心理的一个锚点,影响着人们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态度和看法。
基于这种对传统法律规定、法律实践和法律文化的考察,笔者认为在适用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规则、综合考量是否构成条款中要求的情节恶劣时,可以参考古代判例中的决定少年儿童是否免除死刑的考量因素,将主观内容作为核心的判别标准。具体到各项主观考量因素的判别尺度上,人民检察院在核准追溯或人民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在案件符合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年龄、罪行、结果等要件的情况下,可以参考以下标准认定是否构成情节要件:(1)对于对犯罪行为具有直接故意尤其是对使用“特别残忍手段”具有积极追求态度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倾向于认定构成情节恶劣;对于间接故意犯罪,可以考虑认定不构成情节恶劣。(2) 对于蓄谋犯罪尤其是蓄谋使用“特别残忍手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倾向于认定构成情节恶劣;对于临时起意、激情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考虑不予核准追诉。(3) 对于犯罪故意最初由第三人引起并在后续过程中主动进行相应犯罪行为,但犯罪行为未严重超过他人授意范围的未成年人,应当倾向于认定不构成情节恶劣;但该未成年人在犯罪过程中实施了超过最初犯意内容的行为或显著重于预期的犯罪结果的,则应当倾向于认定构成情节恶劣。不言自明的是,认定情节是否恶劣应当进行综合评判,而不能仅着眼于案件中的某一个考量因素作出片面的判断。(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于浩 马淑婷)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7月上(总第205期) 法治新知栏目】









